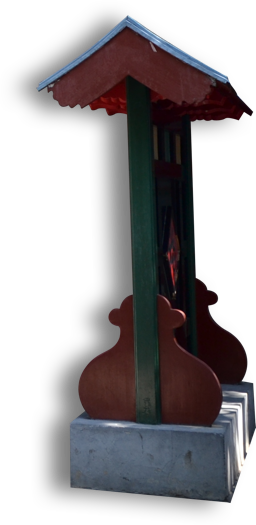创作成就
老舍作品体裁多元、成果丰硕、特色明显。然纵观其全部作品,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的格外关注为其主要成就之一,因独特的语言风格而成为京味文学的源头亦为其主要成就之一。谨此便对这两项主要成就进行介绍,其余方面的无穷意蕴,便交予每位读者自行品味。

一、对文化批判与国民性的关注
老舍对文化批判的关注几乎可在他每篇作品、每个人物中得到体现。他格外擅长通过对普通小人物的书写映射文化背后的秩序冲突,语平俗而意深远。老舍生活在多灾多难而又急剧变化中的旧中国,他以敏感的神经触摸着时代的阵痛,因此才有了他笔下一系列中国的市民形象:他们是住在城里的乡下人,骨子里流淌着守旧的封建宗法思想的血液;他们善良却又自私;注重传统礼节却又因循守旧不知变通。例如,《四世同堂》里面的祁老太爷就集中体现了北京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因此回避一切政治纷争;他忠诚,因此固执地按照祖宗习俗来办事;他太善良,以致逆来顺受……但就是这样一位固执的老人,在民族尊严受到威胁时也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老舍以此深刻地反映出了在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国民性弱点”及这些弱点被不断改造的过程。
面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城市文明不断演进、外来资本主义逐渐侵蚀生活的局面,老舍也同样保持着审慎的反思:《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都是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在情感上却仍身陷封建守旧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这些人物在老舍的笔下,其历史背景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艰难时刻,具有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自然,老舍也塑造了如《二马》中的小伙计李子荣等具有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等品质的正面楷模,虽仍有天真一面,但着实表明了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文化批判深度。
二、对汉民族语言的继承与创新
作为一代语言艺术大师,除了在文化思想层次方面对文化批判、民族性的关注外,老舍也非常注重民族性语言的使用,进而开创了全新的京味小说源流。老舍的独特贡献在于他的民族化的语言观念, 他从大量的口语中提练出俗白、生动、纯净而优美的文学语言,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老舍的民族化的语言观,在他谈创作的文章中,多有涉及,其中比较集中的有《言语与风格》《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我怎样写〈大明湖〉》《我怎样写短篇小说》《我的“话”》《人、物、语言》《语言、人物、戏剧》《语言与生活》《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怎样写通俗文艺》《我怎样学习语言》《文学创作和语言》等篇。其民族化的语言观,包括强烈的民族意识、俗白的语言风格和多元的审美追求等多个方面。
 运用现代白话语言
运用现代白话语言
首先,老舍认为,要使作品具有民族特性,必须发挥汉语的特长,而最能体现汉语特长的莫过于现代白话语言。在谈到作品的思想性时,他认为首先要在语言上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意识。“不管我们的作品的思想性如何高深,内容如何丰富,假如我们的语言不通俗不现成,它就不可能成为具有民族风格,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他批评一部分作品缺少民族意识,是“因为其中的语言不三不四,没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语言之美,于是也就教民族风格受了损失”。老舍热爱现代白话语言,了解现代白话语言,一生运用现代白话语言,他的作品也极具民族风格,关键在于其语言观中的民族意识。
 俗白的民族语言风格
俗白的民族语言风格
老舍语言观中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对俗与白的民族语言风格的追求。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老舍说“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取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它包含了老舍对文学语言的基本看法,也表明了他追求俗白的语言风格。不过,既然是文学语言,自然不可能只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日常生活中人们口头的原始用语,而需要经过作家这样那样的提炼加工。老舍广泛汲取营养,经过不断打磨推敲,创造了一种朗朗上口又清脆悦耳、形象鲜明又简练有力、绰约多姿又深入浅出的语言,更加凸现出口语活泼生动的能力和亲切迷人的神韵,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京味语言的韵味
京味语言的韵味
这种对白话、对“俗”的具体应用,根植于老舍所生活的环境——京城之中。老舍是京味文学的经典代表,是北京文化精神的守望者。北京文化不仅是老舍真切的人生记忆,而且是他热切追求的生命理想。《骆驼祥子》可谓老舍京味语言的集中呈现之作,老舍在小说中大量使用儿化词,生动明确地区分了不同语境中的词义,展现出丰沛的感情色彩,体现出浓厚的北京口语风格,生活化程度颇高的词语也鲜活地描述了北京城的城市样貌和人民生活。这种灵动、幽默、接地气的语言运用实开一代风气之先,为后来的京味小说提供了优秀范式。
综上可知,既有活力四射的语言运用,又有深刻肌理的文化反省,老舍作品取得如此成就,获得数十年来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