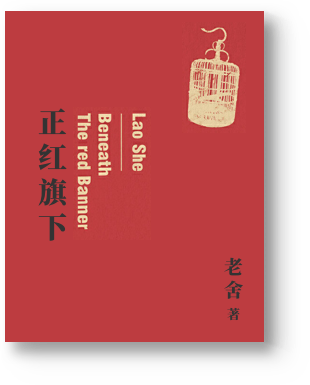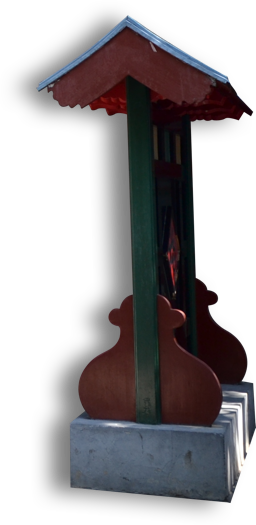与老舍其余体裁作品相比,老舍的小说数量颇丰、成就最高、最能够集中体现老舍的文化底蕴、幽默艺术、生动语言与国民性探索等,也因此最广为人知。老舍一生共创作长篇、中短篇、小说集数十余部,时间跨度涵盖其整个生命,题材遍及民族精神蜕变、文化现象反思、贫苦市民生活等诸多领域,可谓博大精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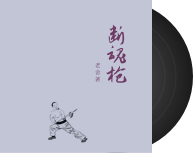
《断魂枪》片段
制作:韩小龙
旅英时期(1924-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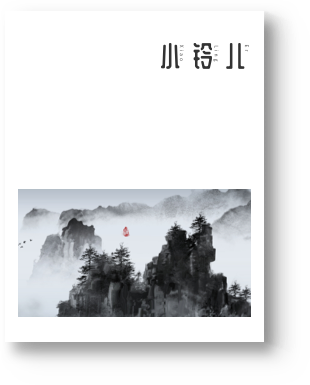
老舍的小说创作始于短篇小说《小铃儿》,却尤其擅长于长篇。1924年,老舍在英国创作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两部作品都以作者熟悉的北京生活为题材,虽然在技巧上仍待改进,加之创作目的不够严谨,但其在创作起步阶段表现出的某些特点依旧极为珍贵,譬如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为其后续小说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调。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来自文明古邦的中国人马氏父子,在英国这个20世纪早期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度中的饶有意味的一段生活经历。《二马》是老舍创作走向成功的标志,它将出身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做了生动、精彩的比照,不但对东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颟顸可悲,做了深刻揭露,也对西方人顽固的种族偏见,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而对中、英两国各自民族精神中的优长,则给予客观评价。
1929年,老舍创作出《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幻想色彩很浓的作品,讲述了生长在新加坡的华侨儿童小坡,和一群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子弟,在现实中相互友爱、在梦境里共同抗敌的有趣故事。作者坦露了向往世间各民族跨越社会和文化藩蓠,彼此尊重、和谐的心迹,也呼吁被压迫民族联合抗争共同迎接新时代。
归国以后(1930年后)
30年代初,老舍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却陷入了对社会现实的忧思与愤懑。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已告失败,军阀割据愈演愈烈,他特别关切的京城满族同胞和各族百姓,生活凄惨之至。老舍于当年夏天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教授,一年后,他围绕济南“五三”惨案,写了长篇小说《大明湖》。该书未出版,全部书稿即被日本轰炸的烈火所焚毁。
 代表作《猫城记》
代表作《猫城记》
1932年,老舍面对江河日下的国事,愤然写出了寓言体文化讽刺长篇小说《猫城记》。地球上的中国人“我”,乘朋友驾驶的飞机到火星探险,着陆时飞机失事,只剩“我”一人活着。在火星上的“猫人”国家里,“我”亲自观察了猫国病入膏肓的文化百态,目睹了猫国在“矮人”国军队入侵下的亡国灭种经过。作品充斥着悲观情绪,而作家意欲表达的挽救式微文化和衰弱国家的强烈愿望,也很容易被读者体察。

 代表作《离婚》
代表作《离婚》
1934年,老舍完成了长篇小说《离婚》。作品通过对民国前期北平城某财务所几个小科员家庭故事的叙述,展现了市民阶层“日常生活哲学”的精细与酸腐,以及其间种种灰色人生的无奈和熬煎,也鞭挞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官僚机构坏。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它用大量幽默笔调写出来了令人慨叹的人生结局,幽默未了即悲从中来,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这种独属于老舍的笑中含泪、泪里带笑的喜悲剧艺术风格,就此被基本确立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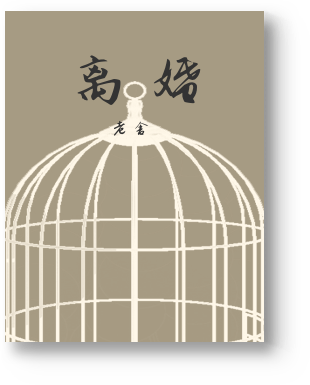
 《柳家大院》等
《柳家大院》等
30年代前中期,中国社会从既有混乱走向新混乱、世道丧失运作章法。老舍对世风的恶化倍感痛心,以多重视角,描绘国民精神溃疡面的持续蔓延,及其人们道德心理的递嬗。在《五七》《柳家大院》《且说屋里》《哀启》等作品里,叙写一部分中国人,要么利用洋人势力欺侮同胞,要么张惶地避让外寇锋芒,连起码的爱国之心也谈不上了。《抱孙》与《眼镜》则勾勒出了国人在20世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之际,依旧盲目排斥科学的可悲情状。《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善人》《牺牲》等,对某些伪善“道德家”和“学问家”,做了无情揭露。《柳屯的》浓缩了一个乡村女恶霸的发迹和败落史,女主人公不断变换两副道德面孔的伎俩,被作家勾画得入木三分。

 中短篇尝试
中短篇尝试
老舍认为,中短篇小说“最需要技巧”。所以,他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微神》使用了朦胧诗般的意境设置,写失恋男青年为了索求故去的心上人,导致一场梦境中的戚戚寻觅。《月牙儿》像一首回肠九转的叙事长诗,作者追踪着女主人公的心理历程,借鉴诗歌艺术的多种手段,将柔美的抒情、哀婉的意境、洗练的语句、短峭的章节乃至出色的象征融为一体,如泣如歌,催人泪下。《我这一辈子》则把白描手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既不乏幽默,又处处被镀上一层冷色。
这一时期的《断魂枪》是老舍短篇小说中的扛鼎之作,作者以简约、深致的格调,摄录了武艺超群的国术大师沙子龙,在经历了声名显赫的前半生之后,毅然让自己以及一身绝代武功淡出人世、淡出历史的感伤故事。 《断魂枪》在构造作品时,巧妙运用了“时空余地”,故事小而又小,所倚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却异常丰厚,故能取得言简意赅、大气包举的效果。

 代表作《骆驼祥子》
代表作《骆驼祥子》
1936年,老舍向世间奉献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集老舍多项艺术优势于一身的作品,也是使老舍最终确定小说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作。30代的中国文学界,藉此重新发现了老舍,老舍也因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最优秀作家之一的位置。《骆驼祥子》这部现代市民文学永不褪色的经典之作,与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鼎足而三,共同托起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殿堂的巍峨拱顶。

抗战时期(1937-1945)
1937年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开始。在领导“文协”会务工作的同时,老舍还以笔为枪,投入战斗。抗战期间,他又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偷生》、第二部《惶惑》,中短篇小说集《东海巴山集》《火车集》和《贫血集》。
 代表作《四世同堂》
代表作《四世同堂》
1948年,老舍一生中规模最宏大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正式创作完成。作品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组成,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叙述了由北平陷落到日本投降 8年间,发生在这座历史名城“小羊圈”胡同中一系列故事。牢记民族被征服的惨痛历史,反思被征服状态下的国民心理弱势,是这部作品彼此相依的双重主题。《四世同堂》架构恢弘,布局匀称,聚散适度,气骨凝重,是一幅超大规模的艺术画卷,上百号或主要或次要的人物形象,均被描绘得十分真切生动。老舍曾将这部小说,看作自己“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战后回国(1946-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老舍到美国讲学并继续写作。他又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写的是曲艺艺人方宝庆一家,在抗战期间漂泊南下,在陪都重庆卖艺渡日的遭遇。《鼓书艺人》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像一方路标,指示了作家在创作思想上的转轨方向。小说异常明确地抨击黑暗政治,鼓吹民主精神,讴赞进步战士,都反映了作家在受到左翼文学原则积极影响之后,写作中出现的新特点。

建国以后(1949以后)
 未竟稿《正红旗下》
未竟稿《正红旗下》
建国以后,老舍依旧以高度的热忱投入写作,但此时期创作则以散文、曲艺、戏剧为主,其晚年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小说艺术,悉数展现在1961年命笔的未竟稿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之中。这是一部家传体作品,描摹了清代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的生活场景,映衬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京城旗人社会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向。《正红旗下》的语言洗练晓畅,风格幽默诙谐,情趣雅俗兼得,尤其是在勾勒清末京师市井民俗方面,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深广蕴涵。这部作品,只写出了近11章约 8万字,看上去还很像是一部长篇巨制的开头,作者便搁笔了。这部远未完成的作品,成了老舍文学生涯中沉甸甸的压卷之作,成了这位举世公认的“人民艺术家”留与世间的艺术“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