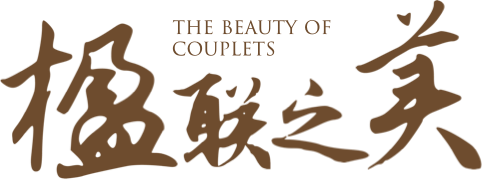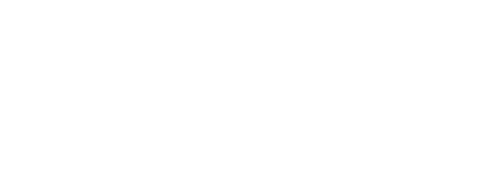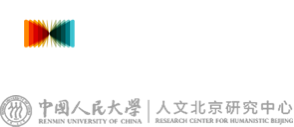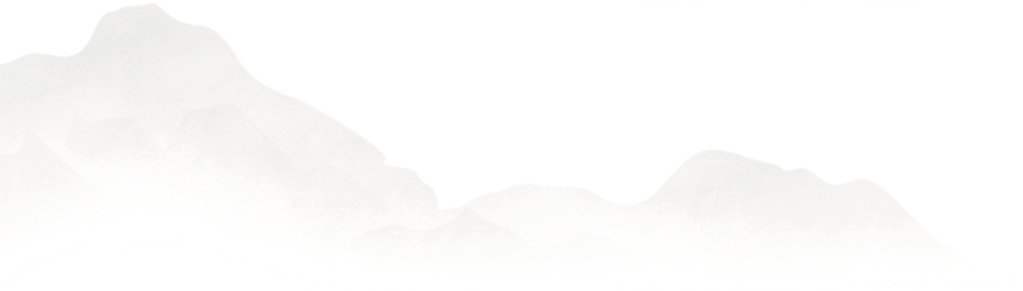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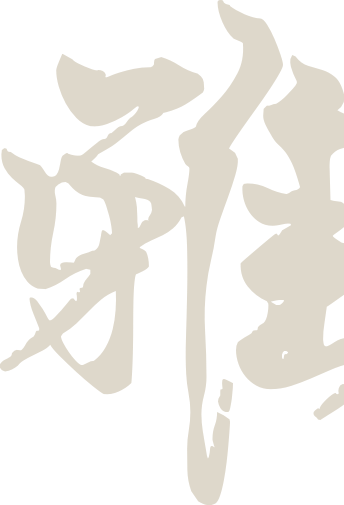
文本
在《起源》一栏中,我们充分论述了作为文学作品的楹联的发展历程,其艺术特征与价值在此过程中自然显现。比如,其发源于对偶句式,而对偶句式正是从各种“雅文学”中孕育而来的,《诗经》、《楚辞》、汉赋、骈文、格律诗等等都提供了对偶句式的丰富实践,楹联的文学性也正是建立在这些“雅文学”的基础上的。“雅文学”能表达的主旨、描写的内容、运用的技巧,楹联同样可以展现,如余维翰《福石山庄联话序》所言:“联语者,诗赋文辞之绪余,文人之结习,未忘其尽心力于于斯道者。”
当然,楹联自有其特殊的性质:在其他文学体裁中,对偶句式只是其中一部分,它的传情达意受到上下文语境的限制;而在楹联中,对偶句就是其全部,它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发挥其艺术魅力,不仅不受其他限制,还必须尽可能浓缩、精炼,此外还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字技巧,因而具有典雅含蓄的表意效果和不拘一格的表达方式。
因此,楹联是一种既包含“雅文学”魅力,又具有自身的独立和“俗文学”特性,下面我们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