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近百年,在这个农业大国的大地上,传统手工业者备受尊重,譬如钉秤的、箍桶的懒车的、修钢笔的,他们掌握了农民所不懂的技术,在不同年代各领风骚。只有补锅匠,在哪个年代都是尴尬的。5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还记得一部年代久远的花鼓戏电影《补锅》,讲的就是丈母娘嫌弃女婿是个补锅匠,想棒打鸳鸯,年轻人突破世俗观念走到起的爱情故事。“革命只是分工不同”的主题虽然鲜明,但补锅匠留给人们的依然是屋檐脚下蹲,一脸墨黑尽灰尘(电影台词)的职业形象。
发展现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连普通人家都早就改用不锈钢锅,甚至高压锅、电饭锅,一般还很少坏;即便锅坏了,一般人大多是扔掉了事。于是,补锅匠生意越来越淡,不得不转行;有些人游走到城市,成为都市里的边缘人,在棚户区、桥洞或小巷里,苦守着一片小门店,勉强谋生。

工作过程
补锅属于小五金行业,在那个大一统的时代,属于没被政府整合又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手业者,政府也征收税收和管理费。所以进入这个行业还是有门槛的的,当学徒是要交学费的,核心技术也不轻易教人,只能靠“目识”去偷师。除了目识好,也好靠经验积累。当时那么多的补锅店,技术也是有分高下的,譬如一些技术高一点的活,别的店做不了,只能指点介绍到某某店修理。而这些核心技术,现在老王说出来,不过八个字而已:圈圈押押,锤锤钉钉。
补锅大抵有两种方式,铝制品的用打栓塞漏,一些金属则需要点锡热合。
打栓
以前没有现在这种现成做好的铝栓,只能用电线里的铝丝,剪断后加工成钉帽来用。如果锅底是裂成条缝的,就要做个胡奇搭(工字理的材料),两边打压实,就不会漏水
点锡
铝制品不能点锡,而像家用的水、面盒、白铁桶坏的,就要点锡。要生个炉子,让盐酸和锡水起化学反应后,再用红铜枪来易热合。

点锡是关键技术
补锅是行业的通称,一个补锅匠,同时还必须是一个所不能的修理工:算盘的几个铜角坏掉了要会钉;铜梳、饭勺折断了要会接;扁担开裂了要会押.…都是些触类旁通的拓展业务,关于生活和劳作的。

农具制作,做得最多的就是农田灌溉用的粗桶(水桶)莲蓬,用的基本都是现在俗称废品的边角材料。牛奶罐是最厚实的素材,但不是想要就有的,“现在牛奶罐到处扔着没人要,但当时在农村哪能看到?只能去汕头买,拿回来修修剪剪用了。”老王说。边角废品一直是补锅铺的主流,后面才有了日本进口的整块的三厘板(镀锌板)。在“文革”期间,老王曾经引领行业潮流,买了一张,花了十几块钱,怕被人说是暴富户,藏在邻村的外婆家,需要一个什么材料了,就先量好尺寸,晚上再偷偷去外婆家剪。
除了农具,生活用品也是补锅铺的手工范围,比如小茶锅。现在回想一下,你应该还记得那种锅身扁椭形的、带着木头把柄的煮水小茶锅,这个小茶锅,早期也都是手工制作的。把铝皮包在木头模具上,用专用的工具慢慢捶打,差不多要做几个小时,一个卖一块多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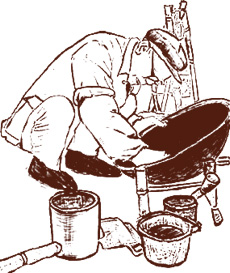
补锅匠就是这样,只要摊子没有铺下来,就活街选边
走边吆喝,吼那一嗓时,颈子仲得长长的,青筋凸起来
像黄桷根,声音又似公鸡打鸣,“补锅哎
补锅!”
黑娃儿吊在后面,习惯性地把火钩、火钳手里,那既是
工具,又当玩具吧。人太小,总是想方设法要玩一玩的。
他主要就干钩钩火、拉拉风箱一类的杂事儿。
四十年前的旧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补锅匠的行头,用一副挑担挑了。一头是风箱,上面
再放一木盒,装些工具杂物;一头挑炭炉、柴火、坩埚等
等。等于一担挑了两木箱,箱的两面分别用“人”字形的
长竹块儿夹住,顶部拴一小截绳,供扁担插入。待要生火
千活儿了,风箱与炭炉之间用一根铁管或是竹筒把它们连
接起来,接头处用稀泥一糊,堵住气漏。
这目子苦,”补锅匠常抱怨,“肚皮吃不饱不说,
一天还要走好几十里路,从天蒙蒙亮就挑担上路,有时熬
到夜里才有得吃。”据说,补锅匠比起叫花子也好不到哪
里去,他们也是“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居无定
所,流浪一般。
补锅是以疤计价,而涧眼的大小、丝缝的长短却颇多
计较。早先的时候,一疤一角,以后涨了一些。
谁拿来漏锅,补锅匠总要先用一小铁杆,在漏处“磕
磕磕”地敲打,刺探,除去周围的铁锈和朽坏的部分,
样,小洞就变成了大洞。女人们常为此和补锅匠发生口角。
“耶耶耶,你是在打洞,还是在补锅哟?”女人的眼
睛睁得老大。
补锅匠已经习惯,永远是一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
清”的无可奈何样:“这些烂掉的地方不去摔,今天补了,
你明天还得补。”然后补充说,“你信,还是不信?
女人噎住了,谁愿意吃眼前亏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