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苏州科大后勤饮服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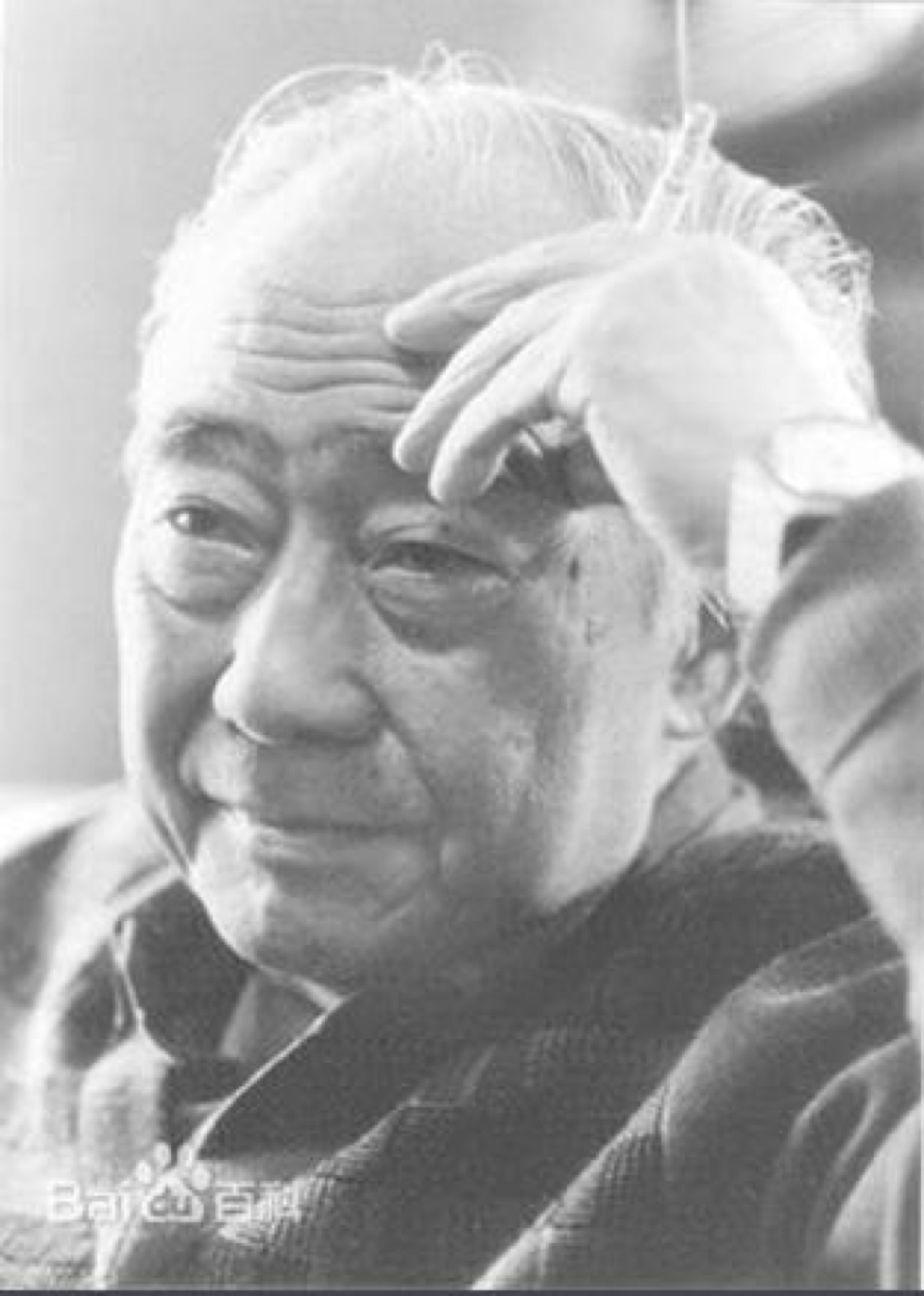
提起汪曾祺,人们都尊称他为"汪老",不过,如果隔壁的某个老张遛弯时碰见他,招呼他一声"老汪头",或是某个女伢子奶声奶气地喊他一声"汪老头",我猜汪曾祺一定不以为杵,反倒会笑眯眯地点头答应,兴致盎然地攀谈几句。这是他的性格,亲近自然万物,平等相待,甚至还怀有一丝天真的孩子气。
为人处世的态度常常不知不觉的渗透在饮食观念上。有的人舌头特别执着专一,昔日张季鹰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乡,非家乡食物不足以慰衷肠;也有的人舌头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汪曾祺似乎是。虽然家乡高邮的咸鸭蛋和野菜是好的,不过尚年轻的"小汪头"怀着勃勃的兴致、随着人生的流转品察各地风物:昆明的菌子和汽锅鸡、北京的豆汁儿和烤肉、张家口的口蘑和马铃薯(号称是吃过最多品种马铃薯的人)……它们在他的笔下凡俗而有灵性,平常却有情味。这容易让人联想起他上小学时放学路上的情景:在回家必经的那条曲曲弯弯的巷子里,他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在饮食的路上,他也喜欢东看看、西品品,有时候还搞搞考据,比如咸菜的起源,苦瓜是瓜吗,虽然大多无果而终,他也不以为意。他对待生活和食物的这种态度可以用他两篇散文的题目来概括——"随遇而安"和"自得其乐"。
其实不仅是出生、学习和工作地方的食物,对于有机会到达的一方风味,他都要试一试。福建的泥蚶、杭州的鱼生、上海的醉蟹呛虾,沁着血的内蒙羊肉,生的、熟的、半生不熟的都可以招呼,甚至古代普遍吃而现在不常见的"葵"和"薤",亦觉别有滋味。汪曾祺自己曾夸口说什么都吃。他还劝人:"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是如此。""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有些吃家仅限于吃家,不一定是玩家,但反过来似乎大多数玩家都是吃家。比如文物收藏家、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先生,懂吃、善做、善品评,有"烹调圣手"之称。汪曾祺也莫不如此,除了是美食家、作家,他搞京剧、擅绘画、精书法,个个都玩的不俗。甚至还能看风水、看相。大概除了天赋家世以外,这与他们宽杂的生活态度也不无关系。汪曾祺说过"生活很好玩"。
出现在汪曾祺笔下的常常是些平易近人的食物,比如萝卜、豆腐、野菜、韭菜花,很亲民,但因为见闻广博,体察真切细致,一个不起眼的食材往往在腾挪进退中呈现出兴味盎然的丰富意趣,虽一块豆腐也有七十二般变化,而他独特传神的语言亦令人口齿生津。汪曾祺的文字明白如话,不事雕琢,但却别有韵味,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自有一派天然的意态。以这样的文字来写美食,自然看的人赏心悦目、兴味十足。
此外,汪氏的写食散文还有一个实在处——可以当菜谱用。汪曾祺对袁枚是有点看法的,他觉得袁子才有些食谱只是道听途说,并未动手操作过,言下之意他自己的食谱都是经过实践检验,是经得起推敲的。倒也不虚,汪老头会做菜在圈内很有些名气,有些远道而来的作家进京指名要吃一顿汪曾祺亲自做的饭。就连黄永玉的儿子在吃过汪家的口蘑豆后也在日记里写道:"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把它做的很好吃,汪伯伯很伟大!"不过,也不是人人都那么幸运,邓友梅运气就差了点儿,虽然定是定了好几次,但有些食材总不那么容易临时凑齐(汪曾祺认为烹饪之道原料第一),好容易有一次没改期,邓友梅早早赴约,孰料连人也没见到,原来汪老先生买菜未果顺道在路边的酒店里喝上了,酒喝起劲了就把事儿给忘了。看来这名士风度在别人眼里很潇洒,真落到自个头上可是不好消受呢。
饮食虽易,知味不易,做一个乐天的有趣味的解味人更难,而于汪曾祺,这些不过是水到渠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他是安静的观察者,也是潜心的品味人,还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年少时家境殷实,在饮食上还不算太差。以后外出辗转求学,求职,走南闯北,吃了不少各地出名的小吃。成名后,汪曾祺经常到各处采风、进行学术交流,各地领导也常用当地名吃招待汪曾祺。汪曾祺自然对美食有着不少了解。可是让人啧啧称赞的是:汪曾祺不仅是个美食家,他还是个出色的大厨。
这些在他的小说及散文中均有所反映。
小说《异秉》写的就是做熏烧的王二,《鉴赏家》写了买水果的叶三,《金冬心》更是名菜荟萃。
他的很多散文就是专门写吃物。如《故乡的食物》、《豆腐》、《萝卜》、《昆明的食物》、《鱼我所欲也》、《鳜鱼》、《家常菜》、《菌小谱》……不仅介绍各地美食美味,还详细介绍一些菜肴的烹饪方法。他的这些文章不仅发表在文学期刊上,有不少就是发表在《中国烹饪》上。
汪曾祺的烹饪手艺在当时文艺圈子中很有名。所以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外国汪曾祺研究者来北京采访汪曾祺时,中国文联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在汪曾祺的家中就餐。一次一个法国客人来采访汪曾祺,汪曾祺为其做了道盐水煮毛豆。那位法国佬第一次吃盐水煮毛豆,竟然连毛豆壳都吃了下肚。还有一次一位台湾作家访问汪曾祺,汪曾祺为其做了道扬州菜——大煮干丝。那位客人最后不仅吃完了干丝,连汤汁也喝得精光。
汪曾祺作为大厨最开心的事就是所做的几道菜被客人全部吃光。
汪曾祺做菜很有讲究,比如,做荤菜用素油,做素菜用荤油;不做客人的家乡菜给客人吃;讲究菜肴的时令,树木萌芽的时候做香椿拌茶干,柳絮飘飞的时候做杨华萝卜,桃花盛开的时节做桃花【zhuæ】(一种野鸟)。
汪曾祺对菜的味道也有研究,除了常人所熟悉的酸、甜、辣、香之外,他对菜肴的苦、臭也很讲究。“苦”也是五味之一,苦瓜(高邮人称癞葡萄)就是他常用的食材之一;不少国人就有香的不吃吃臭的爱好,臭豆腐、臭咸鸭蛋就很常见。
汪曾祺作为作家,有时做菜还渗透一些文化内涵。比如,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做蒌蒿薹子炒肉丝,此时配有河豚鱼更好。边做边吟诵苏轼的《惠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满地蒌蒿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汪曾祺在《故人往事》还谈及主人心态对食客食欲的影响。饭店老板的精气神对生意兴衰的作用很大。无论哪个客人也不会看到一个萎靡不振的面孔会食欲大增。
汪曾祺虽已仙逝,他的文学作品占据文坛一席之地毋庸置疑。他对美食的研究也会被人们记住。高邮不少旅游饭店就推出了汪氏家宴,成为宴请宾朋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
“没他,家里的饭就吃不上了。” 汪曾祺谈吃的美文多不胜举,都有一种从容在里头。“他写东西很随意,吃饭却讲究,除了画画,有了空闲就琢磨‘吃吃喝喝’的事儿。”汪朗头微斜着,轻言细语道,像极了汪曾祺的身影。
-
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 小时看京剧《豆汁记》(即《鸿鸾禧》,又名《金玉奴》,一名《棒打薄情郎》),不知“豆汁”为何物,以为即是豆腐浆。 到了北京,北京的老同学请我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问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儿?”我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的,喝豆汁儿,有什么不“敢”?他带我去到一家小吃店,要了两碗,警告我说:“喝不了,就别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我端起碗来,几口就喝完了。我那同学问:“怎么样?”我说:“再来一碗。” 豆汁儿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很便宜。过去卖生豆汁儿的,用小车推一个有盖的木桶,串背街、胡同。不用“唤头”(招徕顾客的响器),也不吆唤。因为每天串到哪里,大都有准时候。到时候,就有女人提了一个什么容器出来买。有了豆汁儿,这天吃窝头就可以不用熬稀粥了。这是贫民食物。《豆汁记》的金玉奴的父亲金松是“杆儿上的”(叫花头),所以家里有吃剩的豆汁儿,可以给莫稽盛一碗。 卖熟豆汁儿的,在街边支一个摊子。一口铜锅,锅里一锅豆汁,用小火熬着。熬豆汁儿只能用小火,火大了,豆汁儿一翻大泡,就“”了。
-
真切细致,一个不起眼的食材往往在腾挪进退中呈现出兴味盎然的丰富意趣,虽一块豆腐也有七十二般变化,而他独特传神的语言亦令人口齿生津。汪曾祺的文字明白如话,不事雕琢,但却别有韵味,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自有一派天然的意态。以这样的文字来写美食,自然看的人赏心悦目、兴味十足。 此外,汪氏的写食散文还有一个实在处——可以当菜谱用。

